他们冤?
他们俩最该死了!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就真难了!
其实翻遍史书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贪官是一心只管贪的,大都上任时,也是胸怀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毕竟是人,又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饱读诗书的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可以说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马宁远后面跑的。而马宁远又一心要报答浙直总督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严阁老的人,正所谓一环扣一环,扣在最后还是一环。
包括严嵩,当首辅的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没想过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别人,爬得越高权力越大,也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权力以获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终爬到顶峰,无路可爬。
自古权利跟义务是划等号的,严嵩掌握了明帝国一人之下的权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义务。所以,当大明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严嵩!
要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严党提出了“改稻为桑”国策,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同,随后便严格推广起来。可以这样说,这条政策的出台,单从设计的路线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了最终落实政策的基层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级官员,他们怎么去发动老百姓推行这项政策的执行是关键!
二、
“改稻为桑”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军士去踏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了。
可以说,这期间的三个月,马宁远、常伯熙和张知良没少对百姓费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踏苗的损招,不然马宁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们还把新安江的堰口给堵死了,当然,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弃种植水稻。
其实当时胡宗宪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愿改稻为桑,那最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这样干。
到这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都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不够理智的上级,常伯熙还劝他回去再商量别的办法,别跟百姓硬刚,结果被马宁远威胁拿了他乌纱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从马宁远的话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张知良俩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发话的权力,只能被马宁远裹挟着向前走,除非俩人的知县不要当了。
既然不用这两位知县出面硬刚,有上级在现场亲自指挥,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退缩的可能性。尤其是马宁远,总是在放狠话,什么人都死绝了也得改,什么自己就站在这: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三、
可以说,到这时候为止,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都不用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俩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为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
为什么说,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后,必死无疑呢,下面听杨角风来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毁堤淹田的命令是严世蕃下达的,就是因为胡宗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朝廷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所以,这条命令并没有直接下给胡宗宪,而是瞒着胡宗宪下给了郑泌昌和何茂才。
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让计划落地,首先得拉拢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杨金水,这一点两者利益一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便是找执行者,以及日后东窗事发后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因为他们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当然得跟当地的最高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啊。参考后来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没办法。
记住,到此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是跟马宁远捆绑在一起的,真正让马宁远下定决心干蠢事的是杨金水的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但后面两个知县的做法就彻底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宪按哪种方式汇报毁堤淹田之事,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都必死无疑:
按照小阁老的想法,这次新安江决堤,把责任归结于天灾。可是,遍观史书,任何一个地方发灾,不管是什么原因,父母官是必须要到现场赈灾的。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处理大灾,那么省级,朝廷都得派钦差前来处理,没有例外。
而这次新安江决堤,按照后来海瑞查实的情况是:
“一夜之间,整个淳安半个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余人,无家可归三十余万!”
这已经是大灾了,一夜之间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马宁远尚知道跟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饿死人,二是不能让胡部堂下不了台,当然,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后来胡宗宪是掘开了淳安建德两处口子。虽保住了其他几个县,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导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当胡宗宪跟谭伦在前线赈灾的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跟郑泌昌和何茂才喝酒庆功,这就是找死,日后不管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他俩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句神来之笔,当马宁远讲自己如果还在这里喝酒,那就是没了心肝,扭头就要去找胡宗宪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问:
“我们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这个地步,还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小阁老的理论,把决堤按天灾来算,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也难逃一死,除了救灾不力以外,还有另外一条理由,这一条后来胡宗宪也讲了:
同样的暴雨,同样的江河,临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汤,我们这里这个谎怎么圆?
不仅胡宗宪不信,当时的河道监管李玄也不信啊,当时他就找杨金水了:
“干爹,干爹,九个县,九个县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决口,这是要害儿子,害干爹您呐!”
他都清楚,这种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让新安江决堤,肯定是人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么作为淳安和建德两县,修堤到自己管辖范围时,必然会经手参与。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俩的头,事实上也是以这个理由砍了他们。
这还是在天灾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祸,那他们俩更是无处可逃,因为这个堤就是他俩参与决开的,还是后来海瑞的审讯何茂才时记录的口供:
“据查,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原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在端午汛到来之前便带着你臬司衙门的官兵,守在九县每个闸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涨,九个闸口同时决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记住,这俩知县竟然糊涂到带着士兵,挖开口子,淹了自己管辖的地盘,这种父母官,不杀怎么安抚民众?
历来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后,先干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给百姓交代。
那么淳安和建德的这两名知县,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马宁远,停止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说服不了,可以当场辞职不干,以马宁远的脾气,会批准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毁堤淹田的这个动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么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大员,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去,即使是他们刻意为之,也必然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复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么谁会首当其冲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幸亏胡宗宪牺牲了这两个县。如果没有处理,任由九个县被淹,那么其他七个县的县令,脑袋也就跟着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马宁远的死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胡宗宪以他们三个的供词,逼迫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在自己报的河堤失修奏折上签了字。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供词做威胁,他们三个哪里肯这么容易就范?
常伯熙和张知良临死前,还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们冤枉啊!”
你们冤枉?
你们最该死了!
马宁远是胡宗宪的忠实手下,被任命为杭州知府,此人从为官为人上面来说还是不错的,一心在干事,但此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下面的百姓,而是为了报答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做出来的事情即蠢又莽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自己就说过,他活是胡宗宪的人,死是胡宗宪的鬼。而胡宗宪却是严嵩的手下,严嵩为了弥补国库亏空,严厉要求浙江地区推行改稻为桑的农业政策,但老百姓却一百个不答应,导致在作战第一线的马宁远压力山大,为了不给主子胡宗宪抹黑,只能动歪脑筋,直接把老命给赔上了。马宁远居然没有把直接命令他毁堤淹田的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位上级给供出来,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想,他的确不能这么干。
马宁远为了推行严嵩改稻为桑的农业政策,可以说是做到了丧尽天良,他把自己都说成了天下第一罪人,他先是纵马踏苗,后又按照郑泌昌和何茂才两位省级领导的指示毁堤淹田,数万百姓顷刻间领了便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表达他对胡宗宪的死忠,他的人生观就是士为知己者亡,这一生足矣。毁堤淹田是他背着胡宗宪干的,直接命令是从省级官员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人那里发出来的。恰恰这两个人都是严嵩的党羽。最终马宁远成为了胡宗宪的白手套,死到临头却不能反咬出郑和二人,这恰恰是胡宗宪的安排。既然是胡宗宪的指令,马宁远自然不会反咬这两位上级。
胡宗宪出于全局考虑,不想把事情闹大,将杭州知府马宁远为首的4名官员先斩首,然后再上报,以便尽快息事宁人。如果让马宁远反咬郑泌昌和何茂才二人那就是直接打内阁首富严嵩的脸,打严嵩的脸,恰恰违背了胡宗宪的宗旨,胡宗宪可以不当一个名臣,但是他不想做负心之人,他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严嵩的党羽。
马宁远可以说是慷慨赴死,死前向胡宗宪提出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他的家人安全,胡宗宪答应了。如果马宁远反咬郑何二人的话,自己肯定是保不住自己家人的,必定会被满门处决。马宁远身为杭州知府朝廷命官,根本没有考虑过下面的百姓为什么不愿意服从国家政策改稻为桑。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在为上级考虑。马宁元又莽又蠢,为什么胡宗宪还要用他?其实他早就成为了胡宗宪想要牺牲的一颗棋子。胡宗宪不可能不知道马宁远上头的郑泌昌和何茂才是何等角色,他养马宁远这条狗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替自己挡枪子。政治真是太可怕了。
杭州知府张印立
张 未 弛
明朝最后一任杭州知府姓张,名印立,字参我,乃是山东省临朐县大郝庄人,为邑乡贤张显儒之长子。崇祯十年,进士及第,后官至杭州知府。明祚既倾,挂冠归朐,居宝瓶山下之郝庄隐逸终生。此间先后数十年,其轶闻野说,漫布朐境,流传民间;虽不见经传,却久传不湮。故今记之,而飨诸君。
寒窗苦读嵩山寺
崇祯初年,张印立与来仪共读书塾。塾中学子甚众,而学业优异者,惟来仪与张印立也。塾师喜之,厚望寄之,倍付心血以授其业,但等考期,博取功名。
崇祯三年,乡试开科。塾师料其学业已成,功力已就,遂命邑庠同赴省城,以应乡闱。结果,来仪一举夺魁,考取解元;而张印立名落孙山。归,塾师怒,责罚戒尺二百;从此发愤,下帷嵩山龙泉寺,苦读寒窗三载,未归家门一次;磨穿石砚两方,写秃毫笔数十。崇祯六年,再赴乡试,与邑内张涵、冯士标同科中举。及至崇祯十年三月,张印立独领风骚,先于同科举子,考取刘同升榜进士。塾师甚悦,褒其有志;复责来仪,再应会试。迨至崇祯十三年,来仪方同冯士标考取庚辰科进士。
清朝初年,张印立重游故地,遂作《龙泉寺诗》曰:“嵩山山下海门开,万古幽萝映绿苔。榻下龙窥丹灶火,池中月浸紫霞杯(bai)。渔郎不识花津远,桂子方从鹫岭培(pai)。自是千秋文豹地,半檐风日任徘徊。读其诗,思其意,“想其芸窗攻苦,月锻季炼,炉火纯清之候,实有触发于寺中”者也。此乃清道光三年进士刘清源先生在《重修龙泉寺碑文》中,对张印立下帷绝编,寒窗苦读的评述。
衡王府内求功名
张印立进士及第后,初仕北直隶藁城县知县,继转南京户部浙江司主事,两督饷楚中江右,再任南京户部陕西司郎中。恰于此时,不幸忽至,萱堂急逝,回家守制。及至满孝三年,吏部却未起用,皆因人多阙少,候补无期。张印立苦闷家中,邻人出谋曰:“当拜婶母!”婶母朱氏者,乃衡王之女、郝庄仪宾张宗孟(号太岩)之室也。及至邻人怂之再三,张印立遂借春节拜年之机叩拜其婶。朱氏早有所悟,道:“后日初三,大侄子随我去青州,见见您姥爷(衡王),求他进京启奏圣上,谋个官阙,重新起用!”印立再谢。
正月初三,朱氏乘轿,张宗孟和张印立叔侄二人各自乘马跟随轿后,奔赴青州衡王府。及至府中,朱氏引见,张印立叩谒衡王。礼毕随衡王入客厅。仪宾张宗孟言明其意。衡王颔首,并出题探其才学功底。张印立即席作答。
衡王颇为赏识,曰:“外甥学底深厚,足可胜任知府之职。这样吧!天下州府任你选!”
张印立惊喜异常,“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否到苏、杭二州去?请外祖大人裁酌”。
“好!”衡王一口应允,“近日我正要赴京师朝拜圣上,顺便奏明此事,再让吏部通融一番,足可事成。大明江山乃是我朱家天下!要做个知府,还不容易?”张印立叩谢不已。
是年元宵节过后,张印立随衡王赴京觐谒崇祯皇帝,遂得杭州知府之职。据杭州市志办公室陈光熙先生提供的《杭州府志》记载:“张印玉,临朐人,进士,(崇祯)十七年任。”盖将“立”字误作“玉”也。
杭州府中挂冠归
张印立官居正四品知府,衙坐杭州正堂,却念念不忘候补待职时的苦闷滋味,遂勤于政事,“不负朝廷,不负百姓,不负所学”,而“牧民有声”(光绪《临朐县志·人物》)以致杭州府辖地方士民佩其为人,服其为治。
是年春天,巡检兵卒捕获盗窃公廪之贼。
张印立坐堂审问。
贼报姓名,“小人名叫何良,因家中断炊,老母待毙,故盗仓廪……”其情可怜!
张印立急忙询问,“家中断炊,究竟是赋税过重,还是天灾歉收哇?”
何良说:“去年天旱歉收,而田赋丝毫未减;加上贼寇猖獗,抢粮夺米,以致家家粮尽囤空,只靠树皮、菜叶度日。家母年逾七旬,已经饿得身肿眼瞎。我这做儿的,眼看不下,才起歹意,来盗官仓……”
“噢——”张印立微微颔首,“盗窃官仓,应是死罪!不过,念你家境唯艰,孝心可敬,本官免究罪责,回家好生侍候令堂去吧!”何良叩谢,起身欲走。
张印立说:“近日本官将欲下察民情,然后实情上奏,求减田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届时,你可来领粮糊口。”贼感其言,涕零而跪,深谢而去。
张印立访察民情以后,果然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当年田赋,允许开仓赈济灾民。此则史志所谓“张印立牧民有声”之来历。
崇祯末年,国运且尽,帝祚日危;连年天灾,饥民遍地;贼寇猖獗,义兵四起。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继之清兵入关,改称大清帝国。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兵下江南,围杭州。张知府率兵民守城,城守多日,却无救兵。张知府身心交瘁,寝食不安,闷坐府宅之内。戴氏夫人侍奉左右,抚慰照料。戴氏者,钱塘士绅戴太公之女,素习诗书,颇有远虑;由府学教授执柯作伐,而成张印立第四房夫人(当时前三房姚、倪、夏氏俱在山东)。
是夜更深,印立已寐;戴氏恹恹,忽闻窗处响动。
戴氏心惊,推醒夫君。二人屏息聆听,似有人走至窗下。正在疑惑,猛听窗处悄语:“知府大人,快快起来,清兵即将攻城,天亮您就无法脱身了!”
张印立惊询:“你是何人?”
“我叫何良,去年春天,我盗官仓,被老爷宽恕饶命,为报救命之恩,特来救你出城。”
张印立及戴氏慌忙起来。戴氏掌灯开门,只见来者身著夜行防箭服,跪地施礼。
张印立急问:“你缘何如此打扮?”
何良抬头仰面,“家母故去之后,本人孤苦无依,才落草为寇。因本人会些武功夫,故作军中斥候兵……”
张知府神色严竣,“起来说话!你进府宅,有人见过否?”
“禀大人,小人练的是飞檐走壁之功,爬城墙,兵丁不知;入贵府,乃是从房顶而来。衙役也未觉察。”
戴氏夫人低声说:“老爷快拿主意,脱身去吧!”
张知府唉声叹气,喃喃自语:“身为朝廷四品官,岂能偷生奔家还?宁为大明守城死,不愿世人骂万年!”
何良促之,“大人,杭州已是兵临城下,南京新帝已亡,但凭本府兵丁,则是朝不保夕;何况浙江巡抚已决计开城投降,天亮可就难以脱身啦!”
张印立吩咐戴氏,“收拾行李,叫醒孩子。”
戴氏说:“为妾一旦同行,必引歹人注意,还是你先走,我卸掉裙钗,隐匿闾巷,投孩子外公家中。”
“那就让书童护送你等。天下太平之时,再去山东老家吧!”洒泪而别。
张印立脱掉官服,露出青丝便装,说:“何义士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说着,手捧官印,直奔知府正堂;将官服、官印摆放公案之上,然后退入堂中,伏身三拜。府内大小官员及衙役侍卫只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张印立起身,站于堂烛之下,环谓众人曰:“鞑子围城,却无救兵。可知国运且尽!而如今,城池将破,败局难收。诸位纵然以死相殉,亦难扭转乾坤,于国于家并无分毫裨益。故请诸位速去安顿眷属,救护百姓。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言讫,众人一哄而出。
张印立匆匆回到私邸,正遇何良出来。
“大人,事不宜迟啊!”何良催促,“北门外兵力极少,您去叫开城门,从那儿可以突围!”
“再叫开北门?贼兵乘势而入,岂不让百姓更罹其害?”
何良说:“大人,如今清兵已破外城。百姓欲逃无门,求生无路。您一旦叫开北门,恰给百姓开了逃生之路,总比堵在城中被杀被辱要好!”
“那就奔北门。”张印立断然发话,忽又想起戴氏母子,“我的眷属……”
“尊夫人已同令郎走了。”
“噢!”张印立松了一口气,方才出堂,领何良去侧院马厩,各骑一马直奔北门;他们出府入巷,只见人们行色慌慌,东躲西藏。
张印立叫开北门,在何良的带领之下,冲过吊桥,落荒而去。原来何良身为斥候兵,既知军中口令,亦有腰牌兵符,所以逢军遇勇,一路畅行,没费多少口舌,便领张印立越过围城兵营。约摸离开杭州七、八里地,何良带住马缰,“大人快走!恕不远送!”说着抱拳揖别。印立还礼。尔后两人各奔南北。一路之上,张印立马不停蹄,直奔山东。及至归朐,坐骑疲困,数日而亡。张印立心中恻隐,深感此马千里奔命之苦,遂依孔子埋马葬狗之习,命家人葬之村西,称曰:马子冢。时隔不久,王、蒋二书童受戴氏差遣,自钱塘归来问安。
张印立念其孤苦无依,而留居郝庄,视若螟蛉,成其家业。此则大郝庄王、蒋二姓之由来也。
至于戴氏母子,则于杭州失陷之后,投族亲以存身。今之浙江张氏,尚有印立后裔。
负明挂冠空余悔
张印立挂冠杭州,弃官而归,本来已触犯“大明禁律”。按照常规:当予治罪。然因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人过问此事。而张印立扪心自责:“未为大明守城死,实感胸中独惭然!不及逢萌东都去,为避纲纪绝人寰。”于是乎!杜门谢客,隐居家中;或出游石门山及沂嵩峰峦之下,寄情山水,吟哦风月;或足不出户,著书立说,撰成《程朱理学析注》十卷、《宝瓶文集》二十六卷以自娱。(不含《西湖杂咏》三卷诗集。)可惜!后因家中失火而焚毁。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临朐人冯溥曾托人捎信,劝张印立出仕满清。张印立心灰意冷,泚笔回函:“命中注定无官运,强而求之亦碍身。负明挂冠空余悔,岂能再做两朝臣?”婉辞谢绝。
总裁骈邑志
清康熙十一年,临朐知县屠寿徵欲修《临朐县志》,遂请张印立、孙席庆、尹所遴纂修。初,张印立谢绝不就,以免恋栈之嫌,而绝贪腥之论。怎奈屠知县恳求再三,两顾舍下。张印立遂至县庠文庙,荐贡生尹所遴任主笔纂修,荐副贡张侗、副监张嘉宾、张奇峋等辅佐订正。而其本人同原江西袁州府同知孙席庆只作总裁之职。此间,张印立居住邑西郭家楼(后称张家庄)之张府别墅,每天步行进县城北门至县衙,裁定篇目,审阅志文,时则提笔斧正,时则撰文点评,尤其对故交同窗——兰阳知县来仪死节之烈推崇、钦敬,撰长文以评之。此志文成四卷,分目四十有余,较临朐第一部官修县志——嘉靖《临朐县志》更为具体、系统,是临朐县第二部官方县志。志书既成,知县屠寿徵赠一对联:“总裁骈邑志,宰治杭州城。”其中,“骈邑志”系指行世至今的康熙《临朐县志》。
张印立,一生坎坷,仕途不畅,尤其杭州挂冠,使其遗恨终生!及至晚年易箦,尚留遗训曰:“终生一憾,杭州挂冠;有负明惠,忆之赧然!”“愿吾子孙:尽忠朱明,勿事鞑清,全我名节!”言辞切切,足可窥其负明之悔,仇清之忱!亦可知其为全名节,不作贰臣之凛烈!
(本文原载2007年3月21日《潍坊晚报》12版“史海钩沉”。作者张未弛乃是明朝进士、杭州知府张印立直系13世孙。)
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人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见夏,而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马宁远之所以不凡,有郑泌昌和何茂才,最主要就是因为牵扯胡宗宪身后的小阁老,天下的人都认为胡宗宪就是严党的一员。
马宁远不反咬郑泌昌和何茂才的原因
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当中,马宁远只是一个杭州知府而已,他也做不了让杭州附近的两个县决堤淹田的决定,然而他最后却背了锅。马宁远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不想让胡宗宪难做,但是他的直接目的却办了糊涂事,最后甚至差点把胡宗宪拖下水,为了不让胡宗宪也被拖下水,马宁远只好一个人承担了所有。马宁远不反咬一口郑必昌和何茂才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想把小阁老也拖下水,大家都认为胡宗宪就是小阁老派来的,他代表了小阁老,同时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是小阁老推荐的。假如马宁远把郑泌昌和何茂才拖下水,最后马宁远不仅可能自己生命得不到保证,就连家人的生命安全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我对此事的看法
马宁远不反咬郑泌昌和何茂才,在我看来真的是无奈之举,马宁远有自己的家人要保全,马宁远有自己的恩师胡宗宪要保全,为了这些牵挂他不能做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然而这都是表面上所看出来的内容,实际上马宁远做的事情一直都是错误的事情,他随波逐流,他助纣为虐,最后也就只能落得个被斩头的下场。古语有言不欲则刚,这是一点也没有错的,做好了自己那么就是无敌的。
总结
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里面马宁远不反咬郑泌昌和何茂才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想把小阁老拖下水,假如把小阁老拖下水了,那么马宁远不仅自己人头不保,而且会连累更多的人。马宁远为了保全身边的这些人,也只好把自己拿出去当成替罪羊。
其实杭州知府马宁远就是信江的管理者。他知道堤坝的毁坏和农田的泛滥。朝廷派来的太监李璇负责监管信江,但他对堤防的破坏和田地的泛滥一无所知。于是李璇为普拉蒂尼李金水而死。同时,他视如天人,杨为了补偿他,让如娘陪他一起去,让他心甘情愿地死去。
当李璇面临危机时,他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杨金水,他必须想办法把他绑起来。杨金水问他:“这世上怎么会有河岸和堰?”李璇马上意识到,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挪用了修河的钱,堤坝才被毁坏的。这是一个人为的决堤,米歇尔·普拉蒂尼·杨金水知道这一点:李远一生最大的幸运是他生了两个好儿子。
一个是李,另一个是,但是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情况其实很复杂。当时唐朝能治理的地区只有关中地区和河西地区。统一天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统一天下,李渊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按照唐元的策略,唐朝应该先拿下洛阳,控制中原北部最精锐的部分,然后慢慢收拾北方的各个角落,最后南下统一天下。
但这一策略,在后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异化。这两个儿子是他建立唐朝时最好的帮手。同时,玄武门事件后来成为李渊一生最大的失败和痛苦。"米歇尔·普拉蒂尼,你知道这一切?"知道就要知道。杨金水哪里敢承认,这只能是对李璇的一种暗示。
有时候知道的少一点对你有好处:“有些东西放在秤上没有四两重,放在秤上有一千斤也打不过!”杨金水说他不会死你,但李璇不傻。既然救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快点把我调走?嘴上答应马上调走,实际上,李璇已经走不了了,他能活下来,不是杨金水说算了,而是胡宗宪。而李和这两兄弟,最终都得以血洗玄武门。其实他们真的不能怪别人。其实最终导致兄弟俩走到那一步的,还是李源自己。
2021年,“迟到”的欧洲杯,谁将问鼎欧洲之巅?众所周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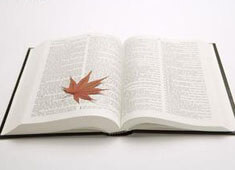
英雄联盟s赛历届冠军都有谁?至今英雄联盟举办了十一届全球总决...
今天阿莫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詹姆斯为什么不能忠于一支球队为什么球迷对...
世界最赚钱的十位运动员,梅西第二,C罗第三1、收入榜前十...
今天阿莫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巴萨误判10个赛季足球比赛有明显的误判,...